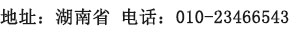公元年,在那个被历史铭记的七月甲戌之时,大辽王朝的缔造者,耶律阿保机,这位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,竟在征服渤海国凯旋、归心似箭的皇都返程路上,悄然陨落了其辉煌的一生。
耶律阿保机辞世之后,四十七岁的皇后述律平挺身而出,接过了皇权的指挥棒,亲自操办起了他的丧葬大典。这位述律平皇后,其实是阿保机姑妈的外甥女,早在豆蔻年华的十四岁,她便与二十岁的表哥阿保机结为了连理。
在庄重而沉寂的葬礼仪式上,上演了一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戏码。述律平竟下令,让人将她的一只手从手腕处利落斩下,随后,这截断腕被恭敬地置入了她丈夫的安息之棺中,仿佛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情感纽带,将生死两界紧紧相连!
这一决策的背后,隐藏着一个深谋远虑的动机:她意在扶持次子耶律德光,使之荣登大宝,成为新一代的掌权者。
这位女士在母爱的分配上,展现出了别具一格的“策略性”——她堪称是一位“偏心大师”。
她携手耶律阿保机,育有三子,长子名为耶律突欲,亦称耶律倍,次子耶律德光,幼子耶律李胡,三兄弟并立,共谱家族辉煌篇章。
在诸多子女之中,她对耶律李胡偏爱有加,这份对小儿子独有的厚爱,仿佛成了母性世界中一个饶有趣味的普遍现象,犹如一种微妙的“定律”,让宠爱幼子之举在女性之中屡见不鲜。
然而,耶律李胡对于那至高无上的帝位,却是无缘问津。究其缘由,皆因他既无名分之正,亦无道理之顺,无论论及功勋还是声望,皆难以跻身前列。
故而,新任帝王面临的选择题,是在长子耶律倍与次子耶律德光之间展开的一场“二选一”大赛。
可以确定无疑的是,耶律阿保机心中的那颗璀璨之星,早已被耶律倍牢牢占据,成为了他心目中的不二之选。
耶律阿保机对那位聪慧且勤学不辍的儿子青睐有加,以至于在公元年,年仅17岁的耶律倍便荣耀加身,被册立为储君。时光荏苒,至公元年,他又被进一步尊封为东丹国王,并赋予了“人皇王”的尊号。彼时,契丹铁骑踏平了渤海国的土地,阿保机遂将其地更名为“东丹国”,并巧妙地援引“天、地、人”三才之古典寓意,将皇太子耶律倍册封为“人皇王”,同时慷慨赐予其象征天子权威的冠冕。此番举动意义非凡,因为阿保机自号“天皇帝”,而其皇后述律平则被誉为“地皇后”,如此一来,耶律倍便稳稳当当地坐实了“双皇之下,万民之上”的显赫地位。
然而,述律平对长子耶律倍并无太多青睐。原因在于,耶律倍深受汉化影响,推崇孔子儒学,力主契丹全面融入汉文化,视儒家学说为治国良方;相比之下,掌控朝纲、权倾一时的述律平,则坚守草原本位之道,矢志维护契丹的奴隶制度。她倾心于传统的草原经济模式,对契丹贵族的传统权益更是呵护备至。
于是,在权衡各种选项后,述律平采取了迂回策略,将目光转向了次子耶律德光,作为她的新选择。
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引领铁骑西征的峥嵘岁月里,耶律德光凭借其赫赫战功,犹如一颗璀璨星辰,悄然间将契丹国的军事大权紧握手中,麾下聚集起了一支庞大的拥趸队伍,其影响力不容小觑。
然而,身为储君的耶律倍,其拥趸数量丝毫未逊于胞弟耶律德光,竞争态势堪称“太子版”的势均力敌。
于是,述律平女士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“清扫行动”,专门针对那些她认为可能给她的“改朝换代”计划添堵的“绊脚石”,毫不留情地一一剔除。
当述律平颁布旨意,要求汉臣赵思温为阿保机陪葬之际,赵思温以机智之语向述律平提出了反驳:“若论起与先帝最为亲近之人,何人能及太后您呢?倘若您愿意前去陪葬,那我赵思温自当义不容辞,紧随其后!”
述律平思维敏捷,迅速回应道:“她并非无意于追随先帝于九泉之下,实乃眼前几个儿子尚且年幼孱弱,国家处于无主之境,她唯有暂且按捺此念,无法即刻成行啊!”
紧接着,述律平下令手下毫不犹豫地挥刀斩向自己的右腕,随后,她以惊人的冷静,指令旁人将这只断腕送入阿保机的棺木之中,以示其“追随殉葬”之志。
这场要求殉葬的壮观剧目终于落下了帷幕,自此以后,不论是皇室宗亲还是朝中百官,皆对述律平女士敬畏有加,视其意志如同雷霆万钧,无人再敢轻易忤逆其意。
随后,述律平再度亲自操刀,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戏——选继承人大戏。
她令太子耶律倍与耶律德光跨上骏马,随即转身面向诸位部落首领,以一副庄重又不失风趣的姿态宣告:“吾之双子,皆乃人中龙凤,帝位之选,于我实难抉择。故而,吾决定将此重任托付于诸位,由尔等来决定,何人更适合登临九五之尊。尔等心中之人选,便是那执其鞍辔之人。”在场部落首领,岂会不明述律平之心思,更何况耶律德光彼时已紧握兵权,犹如龙游浅滩,蓄势待发。于是,这些首领们纷纷行动起来,竞相争抢为耶律德光执鞍牵马,口中高呼:“吾等愿誓死效忠于德光皇帝!”
这简直就是一场权力舞台上的即兴舞蹈,一场悄无声息却震撼人心的“宫廷变奏曲”。
耶律倍眼见败局已定,遂率领一众朝臣,转向述律平恳切陈词:“德光大元帅之德行与功绩,已臻人神共仰之境,举国上下,无不心悦诚服,实为执掌国家大权的不二之选。”
于是乎,耶律德光顺利登基,摇身一变,成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辽太宗,这剧情,简直比剧本还精彩!
耶律德光即位后,对哥哥耶律倍很不放心。
为了牢牢锁定耶律德光作为契丹国主的宝座,其母述律平施展了一系列精妙绝伦的政治手腕。她不仅严令禁止耶律倍重返东丹国,还巧妙地策划了一场人口大迁徙,将东丹国东平郡的民众大规模迁移,随后将该地更名为南京,此举意味深长。更为绝妙的是,述律平将耶律倍“请”到了这座新南京,美其名曰“关照”,实则是对其实施严密的监视与控制,以确保耶律德光的统治地位稳如泰山。
公元年深秋的十一月,耶律倍在重重压力之下,携带着他的爱妾高美人及一摞珍藏书籍,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驶向远方的海船,目标直指后唐。在金州古城,即现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的海岸边,他即将登船之际,回首望向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,心中感慨万千,挥毫泼墨,留下一首意境深远的《海上诗》:“小山凌压于大山之巅,大山却似无力回天。此情此景,羞于面对故乡亲友,吾心已决,从此远赴他乡异国。”
初抵后唐国境,耶律倍迎来了一场盛大的欢迎礼遇。后唐之主李嗣源,动用天子规格的仪仗队伍,亲自迎接这位远方来客,并慷慨赐予其新姓氏“东丹”,以及美名“慕华”。然而,命运多舛,六载光阴匆匆流逝,时至公元年,耶律倍的生命轨迹骤然转折。他被李嗣源的养子,也即后唐末代君主李从珂,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终结了生命。这悲剧的导火索,乃是耶律倍暗中派遣使者,向胞弟耶律德光通风报信,意图借后唐内部动荡之机,引诱辽国铁骑南下,共谋后唐疆土。
公元年之际,契丹与石敬瑭携手大军压境,直逼洛阳城垣之下。李从珂心灰意冷,欲引火自绝,并邀耶律倍共赴黄泉,耶律倍却婉言谢绝。见此情景,李从珂遂遣刺客李彦绅,暗中终结了耶律倍年仅38岁的生命。事后,耶律德光深感悲痛,特地将兄长耶律倍迁葬至其生前钟爱之地——医巫闾山,并追赠其“文武元皇王”之谥号,以示缅怀。
在耶律倍仙逝后的整整一个十年轮回之时,其胞弟耶律德光亦步其后尘,悄然离世。
在公元年的光辉岁月里,耶律德光以雷霆万钧之势,将晋出帝石重贵拉下历史舞台,宣告了后晋王朝的终结。转瞬间,时间轴推进到公元年的二月初一,这一天,耶律德光身着华丽的通天冠与绛纱袍,宛若天神降临,稳稳地踏上了东京汴梁皇宫那庄严的正殿。他端坐在龙椅之上,接受着来自胡汉百官的虔诚朝贺,那场面,堪称是权力的巅峰演绎。随后,一纸诏书,掷地有声,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——国号正式定为“大辽”,历史的车轮,就此驶入了新的篇章。
转瞬之间,那位昔日担任后晋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,竟自行加冕称帝,创建了一个新的王朝,名曰“汉”。这一壮举如同星火燎原,迅速点燃了各路诸侯及后晋老将们的雄心壮志,他们纷纷挥戈而起,遥相呼应。与此同时,中原大地上的广大民众也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驱动,成群结队地挺身而出,对契丹的统治展开了激烈的反抗。
耶律德光面对窘境,只得悻悻然告别封地,踏上北归之旅。行至栾城之地(即现今河北省栾城县境内),竟不期然间疾病缠身,一命呜呼,终年恰好四十六载。
当耶律德光意外地告别了他的帝王生涯,留下了那个至高无上的宝座空悬之时,大臣们纷纷开动脑筋,琢磨着谁来接手这场“王位的接力赛”。一番深思熟虑后,他们慧眼识珠,将目光投向了永康王耶律阮,决定由他接过这沉甸甸的皇冠,继续书写王朝的辉煌篇章。
耶律阮,身为耶律倍之嫡长子,享受着与众不同的待遇。尽管耶律德光对兄长耶律倍态度严苛,却对这位侄儿疼爱有加,犹如亲子般呵护备至。
在历史的某个风趣转角,耶律倍的逃离大戏上演之时,选择了后唐作为他的新舞台。彼时,年仅13岁的耶律阮,与母亲并肩,却并未踏上这场说走就走的旅程,而是默契地决定,在辽国的土地上继续他们的日常剧本。于是,一场关于留守与等待的故事,悄然在辽国的风土中铺陈开来。
在这次耶律德光挥师讨伐后晋的军事行动中,耶律阮有幸伴其左右,这一际遇竟悄然为他铺设了一条通往皇位继承的康庄大道。
在那个决定皇权归属的时刻,皇位继承的舞台上,两位重量级选手赫然在目。一位是耶律德光之胞弟耶律李胡,这位可是述律太后心头那块独一无二的“小棉袄”,宠爱有加;另一位则是耶律德光膝下的长子耶律璟,他同样在候选名单上占据了一席之地,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。
然而,究竟是什么魔力,让朝臣们集体青睐于耶律阮这位人选呢?
表象之下,众人对耶律倍的境遇抱持同情之心,实则更深层次的缘由,乃是众人皆心怀忧虑,生怕述律太后重施故技,借由册立新君之际,再度清除异己,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
面对荒诞不羁的耶律李胡与稚嫩未熟的16岁耶律璟,实权的天平始终倾向于述律太后之手。于是,在耶律德光辞世的翌日,随行的朝臣们迅速作出了明智的抉择,一致推举耶律阮登上帝位,这位新君后来被誉为辽世宗。
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权更迭大戏,再度圆满落幕,宣告着又一次“非暴力革命”的胜利凯旋。
耶律阮登基的讯息,犹如插上了翅膀,迅速飞入了述律平太后的耳畔,瞬间点燃了太后心中的熊熊怒火。她毫不犹豫地指派了“举世无双的兵马统帅”耶律李胡,令其即刻率领大军,踏上了一场旨在“平定叛乱”的征途。然而,这场看似气势如虹的征讨,最终却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收场——耶律李胡非但没有凯旋而归,反而带着惨败的阴影,灰溜溜地回到了都城。
述律平怒火更盛,亲自整顿兵马,准备和孙子决战,双方在横河之横渡对峙,战事一触即发。
于危难之际,契丹贵族中的佼佼者耶律屋质毅然站出,巧妙促成了两代人之间的和解,最终敲定了渡江之盟。在这场权力博弈中,述律平与耶律李胡不得不认可了耶律阮的帝王之位,承认了既成事实。
彼时,耶律屋质向述律平抛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,令她心头一震:“观李胡与永康王二人,皆为太祖与您太后血脉相承之后裔,国之大权犹在自家之手,未曾旁落,您又何必如此这般执着不悟呢?”
然而,述律平对于扶持耶律李胡登基的执念犹如磐石未动,她持续地在暗处蛰伏,伺机而动,精心布局一场旨在颠覆其孙皇位的宫廷政变大戏。
耶律阮机智地洞悉了祖母的谋略,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。他迅速行动,将祖母述律平与叔父耶律李胡一网打尽,并且不由分说地将他们“护送”至祖州的圜土之地,为他们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“长期度假”,实则将他们囚禁了起来。
然而,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耶律阮这位孙辈竟然先于祖母述律平,早早地告别了尘世。
在登基四载之后,公元年的光景,辽世宗耶律阮亲率大军征讨后周。行军征途中的某个夜晚,耶律阮醉意朦胧,不料竟被耶律阿保机之侄耶律察割暗中行刺,不幸陨落,年仅三十四岁。这一宫廷变故,在历史上留下了“火神淀之乱”的骇人听闻之名。
在历史的戏剧性转折中,耶律阮不幸遭遇了暗杀的命运,而耶律屋质则机智地溜之大吉,不仅成功脱身,还迅速集结了一支由救兵与随征军构成的“正义联盟”。在这支联盟的率领下,寿安王耶律璟闪亮登场,他们合力镇压了那场突如其来的叛乱,将罪魁祸首耶律察割一举歼灭,为历史书写了一段别样的“除暴安良”传奇。
随后,帝位花落耶律璟家,他便被历史铭记为辽穆宗。这位耶律璟,乃是耶律德光之嫡长子,如此一来,帝王的宝座再度回到了辽太宗的血脉之中,仿佛是一场权力的轮回大戏。
在公元年的那个六月十九日,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述律平悄然谢幕,享年高达智慧与岁月并蓄的七十五载。其身后事被隆重安排,与伟大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并肩长眠,共赴那永恒的祖陵之约,仿佛是在向世人宣告:一段传奇与另一段辉煌的完美融合,就此在黄土之下继续书写着不朽的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