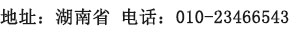栾城好人
文/郭玉芬
年6月7号,我和老伴从千里之外的塞外古城宣化来到栾城,给在石家庄二中读高二的孙女陪读。栾城,我并不陌生。年9月,作为河北师大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,曾被派到栾城搞四清。在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11个月的相处中,我感受到这一方热土上的人们,除了天下农民共有的淳朴、勤劳、善良的共性外,还有诚恳、友善、多情的个性,他们总是力所能及地关爱着每一个接触到的人。我忘不了在辛李庄住在五保户冯二妮大娘家里,每当晚上我开会回来,总会看到七十多岁的大娘在大门口接我;在东牛村,住在赵二秋大娘家里,赶上邢台地震,大娘被震醒后,首先到我住的屋叫醒我。那几天,大娘一直让我和她睡在一起,像关照儿女一样关照我;在康家庄,我不慎丢了钱包,里面装着学校发的伙食费和粮票。房东的女儿秀琴知道后,马上召集小青年开会,发动大家帮我找钱包。并叮嘱他们,我到谁家吃派饭也不许收我的钱和粮票。我的钱包还真被找回来了,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。搞四清的经历,让我终生难忘。每当想起那段日子,我还会哼几句“一根蔓上两颗瓜呀,贫代会上遇亲家呀”,或唱几句《老两口学毛选》。这次重到栾城,我想看一看曾生活过的村庄,找一找当年的熟人。为此,国庆节前我特意打车去了一趟辛李庄。进村一打听,当时跟我跑前跑后的青年积极分子刘增栓、刘铁锁已过世。乳名叫“八十”的还健在。经人指点我走进八十的家。我一叫“八十!”他一下认出我来,一声“姐姐”,竟哽咽了,还是那么亲切。那时,他十三四岁,我刚二十出头,如今都已满头白发。唠起当年的人和事,有说不完的话题。我让他带我到村里转转,看看我住过的院子。村里变化太大了,村里布局都重新规划了,原来的院子已不复存在。街道拓宽了,道路硬化了。家家盖起了新房,格局和城里的楼房一样,再也不是锅台连着炕了。人们的穿着光鲜了,和城里人没什么差别了。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,我要回城里了。八十摘下院子里的丝瓜、玉瓜、石榴,让我带回城里,让他儿子开车把我送到我住的小区。春节前八十打来电话,邀请我去他家小聚,只是因为疫情没能成行。我为村里的变化、村民的幸福生活而欣慰。这一次来到栾城,我更深深地感受到了栾城人的友爱、善良。我们租住在王家庄新村的楼房里。到栾城的那天,正好是端午节,中午,房东老崔送过来一大盘自家包的粽子,一再说如果缺什么少什么尽管去他家拿。看到我们年岁大,又一再叮嘱,有干不动的活,叫上他,千万别累着。我们住下后,他们多次送来豆角、西红柿等各种蔬菜。冬天,他儿媳妇小张分回来大白菜,让我们随便吃,诚恳地告诉我们,他一家吃不了那么多,放烂了也是浪费。我们一冬天都没买大白菜,一直吃到4月中旬。新冠疫情发生后,小张又问我们缺不缺米面,又送来大萝卜。孙女在家上网课,随时需要打印材料,有时打印店不开门,小张几次帮忙打印。有一次,老师下午5点发来试卷,晚上就要考试。我给小张发去